
赫尔曼·黑塞可以说是一位虔诚的信件作家,除了小说、诗歌、散文以外,他还在诸多信件当中留下了自己思想的痕迹。黑塞也是永远属于年轻一代的作家,他不仅与朋友和家人通信,还与他的读者通信。
相比于寄给父母那些兼存尊敬和叛逆的家书、写给文学友人那些真实的喜乐和抱怨,面对读者,黑塞更多是一个“智慧锦囊”,常常从独特的角度答疑解惑,金句频出、一针见血。当有读者要求他多写点战争时事的时候,他认为作家不应被这种“时效”辖制;有读者问他为什么《玻璃球游戏》中没有女性角色,他没有胡诌高深的理论,而是给出真相“作家本人也不见得想得透彻”。
以下是黑塞写给读者的一些生动有趣的信件,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本人对于文学、生命和文化的独特思考。
本文摘编自《黑塞书信集》,经出品方授权发布。
01 ✉️
对一项调查的回答
日期不详
年轻人不 论从事什么工作,不论对工作有什么样的理解,有多努力——他总会从少年时各种狂乱的热望进入一个组织严密、僵化的世界里,而且会屡屡失望。这种失望本身不一定有害,清醒也可能意味着胜利。但大部分职业 ,尤其那些“高级”的职业,现在靠的就是人本性中的自私、胆怯、贪图安逸。只要别太认真计较,低下身子,乖乖听上面的话,就能轻松胜任;可如果他要的、追求的是劳作和责任,那就会十分艰难。
其他的年轻人怎么看待这些事,与我无关。想从事思想工作的人会发现这是一块危险的暗礁。他们不应该逃避工作,尤其是国家组织的工作,而应该去尝试!但他们不能让自己完全依赖工作。在开始从事一种职业之前就订了婚或结了婚的人,习惯了优裕生活的人,职业不会锻炼他,在职业中他不会显得坚强,不会显得足够坚韧,他只会去适应,会生锈。

电影《勒阿弗尔》
美国人爱默生,尽管我对他并不熟悉,但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如果一个年轻人感到心中有崇高的使命召唤,召唤他成为科学家、艺术家、牧师、引领者,召唤他从事思想工作,负起责任,那他就绝不能把自己与物质世界联系起来。他就不应该订婚、结婚,不能享受美食华屋,不能喜爱奢侈和安逸。爱默生认为,做到这些的人,就能够箪食瓢饮,为自己的使命保持自由之身。
能听进去这种话的,从来都只是少数人。但重要的是,就是这少数人中,会有一些我们的年轻人,为了信仰和人生梦想,愿意坚守那三个古老的誓言 (指《马太福音》中提出的贫穷、不婚的童贞和顺从) 。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此。
02 ✉️
致一位要求黑塞多写点“时事”的读者
1939年10月
感谢您亲切的来信。对于您所认为的作家的使命,或者说作家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我并不完全认同。作家与常人的区别在于,比起常人,他要自我得多;他只有践行这种自我,不要顾忌是否正常,不去考虑为了这个他得付出多少,才能成为作家;同样,作为作家他也只能依顺自己那套总是与常情不符的温度和气压。所以我——其实也出乎自己的意料——写出那些诗句,写出那些双行押韵诗和即兴诗之后,不认为关于这场战争自己还有什么可以写的。
不过我还是得顺应自己的要求,也要维持生活。我这么一个上了年纪的、没用的人,从九年前起就着手进行一项创作,要写好这个主题就得完全投入,我将把余生都倾注在它上面。八年多了,我一直在这件事上下功夫,为了精心编织我的造物,其他事情我都渐渐地不管了,它最后是件有价值的作品抑或仅仅是异想天开,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几年来,这件作品的部分内容零星地出版,我得一直做下去,不然这些岁月就虚掷了。

电影《波斯语课》
战争,我们俩都憎恶的战争,它注定要变成“全面”的。打仗的时候,士兵会开枪,学校老师会戴上头盔,面包师也会磨快刺刀,不仅他们,每一个男孩都力争能戴上袖章,他们不想再做毛头孩子,他们想成为战争的一分子。作家越是向这种趋势让步,战争就越有理由来支配他,他就更加远离创作,而对于创作来说,原本就不该存在“时效”这个概念。
03 ✉️
致读者
1945年2月
为什么《玻璃球游戏》里没有女性?
这个问题常有人在信中提出,我却没有兴致回答。因为提出这个问题的读者没有遵守阅读时的首要规则:书里写什么就是什么,阅读并接受它,而不要用自己的想法或期待去度量。如果有人看见草地上有一株藏红花,就问为什么这儿长着一株藏红花而不是一棵棕榈树,这人也许不是真的爱花人。
但每条规则也都会遇到让它失灵的情况。我遇到的情况是,有位女性读者时而好奇、时而责备地问《玻璃球游戏》里为什么没有女性人物,可她的信却带着一种非常美妙的精神气质。总之我打算认真对待这封信,这次不能再回避这个问题。我给了一个简短的回答,由于这个问题总是反复被问起,我将自己回信中的相关段落公开于此。如下:
您的问题很难回答。我当然可以说出一些理由,但它们不过是敷衍。创作并不简单地产生于思索和愿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深层原因,作家本人也不见得看得见、想得透彻。

电影《法兰西特派》
我想建议这么去看这个问题:
《玻璃球游戏》的作者年事渐高,历经多年完成了这部作品后已经是个老人。作者越老,就越是要求精确和真挚,只说他的确了解的东西。作为人生的一段经历,尽管他以前对女性了解颇多,但对于半老的人和已经老了的人来说,她们又离得很远,变得神秘了,他不敢妄言,也不敢相信自己对此还有真正的了解。而男人的游戏,尤其是精神上的那种,他却了解得十分透彻,那才是他自己的天地。
有想象力的读者会进到我的卡斯塔利亚 (黑塞在《玻璃球游戏》中虚构的地名) , 创造出、想象出从阿斯帕西娅 ( 雅典社会的活跃人物,她鼓励妇女到公共场所并接受高等教育 ) 到现代的一切智慧的、精神上又很优秀的女性。
04 ✉️
致高桥健二
1955年5月
亲爱的高桥健二教授先生:
(高桥健二(Kenji Takahashi,1902—1998),日本翻译家,他来信请黑塞为日译版《黑塞全集》撰写前言)
到了我这个年纪,人永远无法知道明天是否还活着。所以我现在就写好了您要的前言。
致我的日本读者:
日本乐意接受我们的科学、艺术与文学,我们欧洲人总是对这种海纳百川的态度感到惊讶。我们看到:最远的东方是愿意了解我们的,愿意接受我们的思想与游戏,向我们学习,与我们做思想上的贸易。可惜的是,我不能说西方的知识界也同样乐于并渴望与东方思想结交并熟悉它。当然,欧洲有吠檀多的追随者,有佛教徒,也有中国与日本艺术的爱好者与收藏家。但这种对东方世界的喜爱仅限于小圈子,在许多情况下是没有结果的,是一种逃脱,从目前西方的困境中逃进一个美妙的梦幻世界。我相信也希望日本对欧洲文化产品的喜爱没有这种逃脱性质。
我是个年迈的、东方学说与观点的热情膜拜者,年轻时第一次与亚洲精神结交也是为寻找避难所与安慰,结交始于印度,始于阅读《薄伽梵歌》《奥义书》和佛陀的讲道。几年后我了解了中国的大师,也与日本建立起某种程度上的个人关系,是通过我表弟威廉·贡德特和其他一些德国人,他们作为传教士、教师与翻译在日本工作。通过这一途径,我特别对佛教远东的形式——禅宗多了一些了解。我总是以一种全新的喜悦及钦佩之情喜欢画家与木刻版画家的艺术,也喜欢日本抒情诗那美妙的生动性与贞洁。就这样,除了我们西方传统外,印度、中国与日本成了我的老师与生命源泉,我很高兴地听到有回声从你们遥远的岛国逐渐向我传来,看到我的喜爱在那里得到回应。

电影《推手》
东西方彼此认真且富有成果的理解不仅在政治与社会领域是我们时代伟大且尚未得到满足的要求,在思想与生活艺术领域也是一种必须,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今天,问题不再是让日本皈依基督教,欧洲人皈依佛教或道教。我们不应该也不愿意改变他人的信仰或被改变,而是开放与拓展我们自己;我们不再认为东西方的智慧是彼此交战的敌对力量,而是作为极点,繁殖力强大的生命就在极点之间摆动。
05 ✉️
致一位读者
1941年11月,巴登
尊敬的小姐:
我将您的信从蒙塔诺拉带到了巴登,我将在此疗养三四周。
您不期望收到回音,我也觉得复信不容易,确实,我作为作家,工作的全部意义就是在“常规”和标准面前保卫并加强个人性,最难的莫过于把人们用其他形式——比如在画里、文学作品里——多次表达的东西言简意赅地复述出来了。
我完全理解您信中的不满。不过,您信中表达的那种渴望,渴望让自己去适应,渴望从众、符合常规,我认为是实现不了的。人可以去找同伴,但对那些非常自我、孤独的人来说,只能以一种司空见惯又带有缺憾的方式去与常规生活和平相处。这样还不如去找一些别的圈子,那些您认为有共同语言的圈子,比如诗人们、思想家们、孤独者们。
如果在别处我们找不到同伴,至少还可以有丰富的、永不枯竭的替代品,就是我们知道永远都会有人是我们的同伴,有人与我们相近,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和语言里,书籍里、思想里、艺术品里,都有他们在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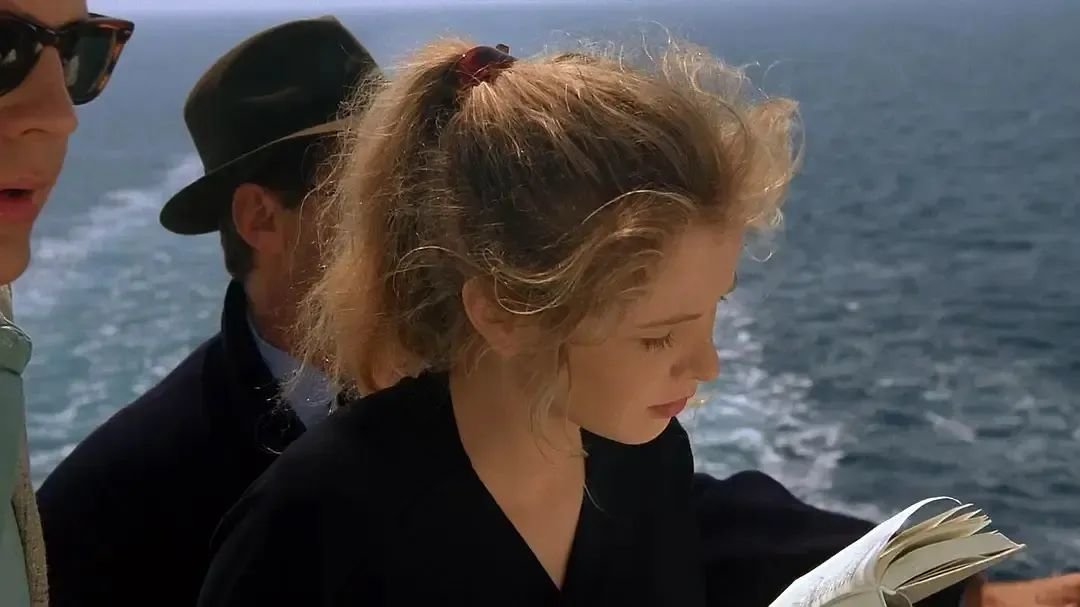
电影《玻璃玫瑰》
努力想跟其他人一样去过所谓“真实”又健康的生活,肯定不是全无意义。但最后这些努力会一再带我们进入一个世界,它的各种价值和标准,我们打心底里不认同。而我们在这中间所获得的,又会从掌中散落。
除了思想家和诗人,还有向我们敞开的大自然,我们可以与另一个世界共振,它没有成规,只向那些赤诚的人、懂得体察入微的人开放。那些只在周末郊游或企业观光中体会大自然的人,大自然对他们来说也只是个模糊的影子。
正巧,我正在分赠小礼物,现随信附上一份。
写得够多了,这么长的信已经超出我所能。

本文摘编自

《黑塞书信集》
作者:[德]赫尔曼·黑塞
译者:谢莹莹/王滨滨/巩婕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世纪文景
出版年:2023-4
,不百骏图 足够坚韧,只会去适应的人,会生锈黑塞相关:
屠格涅夫致信福楼拜:那件俄式睡袍您收到了吗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写作人:天才的怪癖与死亡》的后记。作者哈尔维·马里亚斯用放大镜在才华里寻找古怪,试图用别具一格的角度,打破我们对那些久负盛名的大作家们的刻板印象。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精通多国语言,他长期生活在法国,跟莫泊桑这帮人感情非常好,与福楼拜的友谊直到晚年也丝毫不减。下文刻画了福楼拜和屠格涅夫这对挚友晚年的部分生活事迹。同样作为19世纪鼎鼎有名的作家,屠格涅夫性情爽朗外放,每日有花不完的精..
今天终于读懂了《围城》里的感情线“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围城》钱锺书
她是库里迷妹,更是高尔夫大满贯冠军殷若宁在Instagram上发布的第一篇图文,是她的偶像库里。2021年12月15日,库里成为NBA新一任“三分王”。殷若宁则引用了库里写在球鞋上的格言“I can do all things”(我无所不能)来记录这一时刻。在这篇图文发出的两天前,殷若宁刚刚结束了LPGA(高尔夫女子美巡赛)资格考,并以并列第4名的高排名拿到2022赛季LPGA会员全卡。一年半之后,在女子PGA锦标赛的比赛周末,殷若宁也如那句她写下的格言一样,“无所不能”。北京..
普里戈任去向引发诸多猜测!俄媒:俄罗斯人不会原谅叛徒在俄私营军事集团瓦格纳“武装叛乱”事件平息后,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戈任的去向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白俄罗斯媒体26日称当天发现他出现在明斯克一家酒店。但该消息未得到普里戈任本人或者白俄罗斯官方证实。据白俄罗斯Blizko网站报道,普里戈任当天被人看到出现在明斯克一家酒店内。对此,当地新闻官员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相关的信息可以提供。这条消息十分简短,也没有配图,但众多国际媒体仍纷纷转发。与此同时,普里戈任在瓦格纳..
俄媒:西方欲通过武力夺取白俄罗斯政权据塔斯社6月25日报道,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调查局副局长康斯坦丁·贝切克透露,克格勃已掌握关于外国情报人员的信息,这些人在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训练武装分子,策划以武力夺取白俄罗斯政权。报道称,贝切克在白俄罗斯一台的节目中说:“克格勃知晓正在接受训练的武装分子,知晓训练这些人的情报人员的身份。我们知晓数个以好的名义做幌子、资助恐怖活动的基金会。”他表示,波兰、立陶宛、乌克兰的特种部..
德媒:俄黑海舰队护卫舰换装“二战伪装迷彩”防乌军袭击据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6月25日报道,俄罗斯黑海舰队正在使用一种二战时期伪装迷彩的方式,来保护其作战舰艇,降低被乌克兰无人机或无人水面艇的攻击概率。美海军新闻网站援引卫星图像报道,为迷惑乌克兰无人机和无人艇,俄海军“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在舰首和舰尾刷了一层新涂装。这种新深色迷彩涂装可缩小这艘战舰的视觉轮廓,以此来迷惑进攻方。美海军新闻网站称,这种涂迷彩的方式已经有几十年没人使用了,但在二战期间十..
俄乌冲突令欧洲觉醒:我们的防空系统存在严重缺陷据法新社报道,防空,对欧洲人来说是一个复杂的觉醒,欧洲最近开始直面自己的防空短板。报道称,乌克兰不断地发生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让欧洲国家不得不直面自己在防空上的缺陷。专家们认为,即便欧洲国家想组织起来弥补这一缺陷,过程可能也很艰难、比较耗时及花费高昂。美国航空动力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理查德·阿布拉菲亚说,巴黎航展上防御空中威胁会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他表示:“人们会更多地去谈论导弹生产能力。这毫无疑问..
乌聘请弹道学“侦探”通过残骸识别俄导弹据西班牙《世界报》网站6月23日报道,乌克兰检察机关聘请了一些弹道学的“福尔摩斯”,负责识别俄罗斯军队使用的各型射弹。报道称,在一座位于基辅的小花园里,弹药残骸排列成行。安德里·库利奇斯基一边在一棵棵小树间移动,一边指出K-55的巨大框架——或者说残留的部分。他解释说:“这是一种可以携带核弹头的火箭,射程超过2000公里。”旁边的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残骸。这位专家说:“其中一些是训练用的空包弹,像是用..
汾酒·凤凰军机处乌军反攻伤亡惨重 巡飞弹戳破“豹2神话”截止2023年6月27日,乌军的春季反攻已经持续了23天。在这场攻势中,接受北约训练的乌克兰新编野战旅也首次出现在战场上,而他们装备的“豹2”主战坦克、AMX-10RC装甲侦察车、“布雷德利”步兵战车也出现了相当规模的战损。今天我们邀请了军事专家熊伟老师和俞硕老师,来跟大家聊聊这场攻势的进展情况及其未来走向。可以说,在俄军构筑的“二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防线”面前,乌军撞得头破血流。但纵观近三周的战斗,也会发现,乌..
专访《两种孤独》译者侯健:回归拉美文学爆炸原点,理解孤独《两种孤独》记录了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7年的一次对谈。那时,拉美文学正处于“爆炸”盛况之中,对谈的双方都还是年轻的拉丁美洲小说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刚刚问世,而略萨凭借1966年出版的《绿房子》获得了罗慕洛·加列戈斯文学奖。在这本书的译者侯健看来,现在的读者回过头再看他们五十多年前的谈话,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可以让自己“回归到1967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