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书《声誉》中,“专业读者”唐诺进行了一场有关声誉、财富和权势的思索之旅。他从本雅明之死开始,涉及汉娜·阿伦特、契诃夫、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旁征博引,繁富多彩。
这场旅程末尾,他讨论的是“书写者该过什么样的日子”?这似乎是作为书写者的他的自问,也是对庞大书写群体的生活方式的思考。本文选自《声誉》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文作者|唐诺
摘编|张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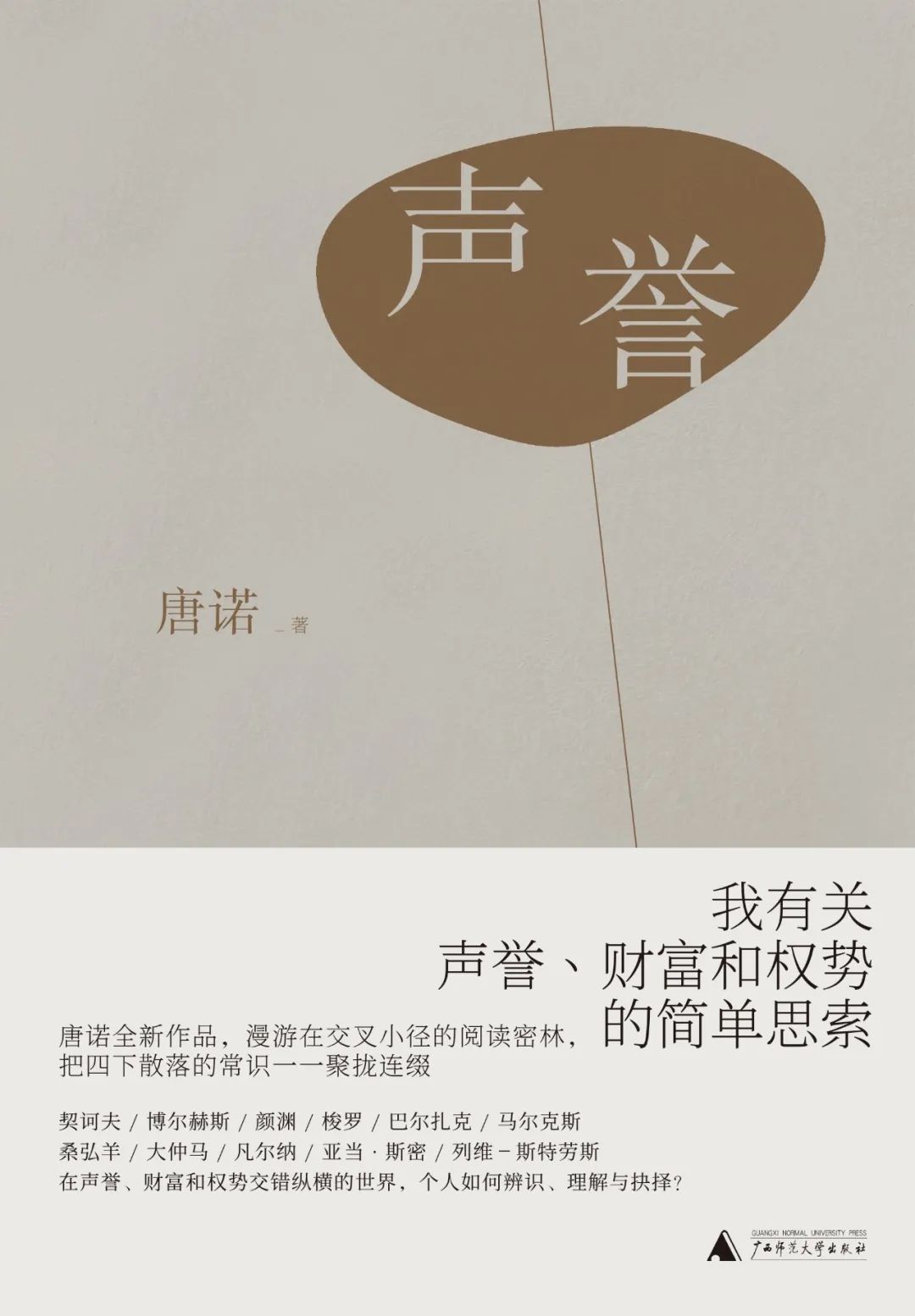
《声誉》,作者:唐诺,版本: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3月
本来,接下来该进一步谈的是书写的公共性,好较周全回答书写的内在驱动之力此一询问,在声誉召唤力日渐可疑并只会再微弱下去的现实情况下。但我试了一下决定算了(废去了五张成稿)——我猜想,那些够好的书写者不会乐意我这么说话,这总是太像为书写一事“请命”了。好的书写者总多出来一些硬颈的成分,他受不了这个乃至感觉反胃,“拜托你们让我也尽点力、让我有机会为大家服务”云云,这是只有候选人才说得出口的奇妙话语。世与我而相违,我相信书写者宁可说书写是单纯的个人之事,这一切只是个人的选择和坚持,完毕。
书写最根柢处当然是公共的,书是公共的形式,语言文字也都是公共意义的——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完全丧失此一可能,书写者最终仍有一个拒绝再说再写的选项,如相传当年骑着牛潇洒出关、完全回归成他一人的智者老子。
所以,我们转为具体地来想这个小问题,时不时有人提起来的——书写者该过什么样的日子才对?好一些、还是糟糕一些?

唐诺,本名谢材俊,一九五八年生于台湾宜兰,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曾与朱天文、朱天心等创办著名文学杂志《三三集刊》,后任职出版公司数年。近年专事写作,曾获多种文学奖项,朱天文誉之为“一个谦逊的博学者、聆听者和发想者”。摄影杨明
1
太过安适的生活
对文学书写者是个局限
如今收在《番石榴飘香》这本很好看的种种书写真相揭示之书里头——加西亚·马尔克斯讲他对书写环境的寻求和依赖,很多更像只是个人的习惯和怪癖,如梭罗讲的,换一个人不仅没必要,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他墨西哥的住家,他说他要求屋内的温度得暖一些(不是容易昏昏欲睡吗?没有那种清操厉冰雪的抖擞之感?),也讲他对电动打字机的无法替代依赖、他近乎浪费的纸张消耗量;甚至,他发现自己对番石榴花香气的奇妙需要,他怎么也写不顺手的这部小说,始终呼之欲出就是少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原来就是空气里的番石榴花飘香......
少来了,我们太知道他的生平了,他是一个最没办法躲到他作品后头的书写者,他的声誉神迹般来得又急又大─在《百年孤独》取得巨大当下声誉和财富报偿之前的长段书写生涯里,我们完全清楚比方他靠四下推销百科全书乃至于人们善意接待的那段潦倒不成日子,当时他如何要求这些?哪里能坚持哪个哪个是绝不能少的?就写吧,像福克纳说过的,最终书写就是一支笔和一些纸,至于福克纳同时也说的香烟和一点点酒,他自己都晓得那是他偷加进去的。
我也知道晚年宛如世界公民或文学共和国公民的纳博科夫用以书写的瑞士旅馆细节种种(相对地,他不大提自己的流亡岁月,纳博科夫正是最硬颈的书写者,不是那种满嘴怨言、成天怪罪异国世界对他不公的哭兮兮之人),纳博科夫也讲,这家以及这一带旅馆正是当年托尔斯泰等一干旧俄贵族书写者的寓居之地,他们有机会就溜出冰封的俄罗斯,这里有较温暖也较多一点自由的空气。
有些人更有这样的文学好奇习惯,会一地一地地寻访这些了不起书写者的昔日故居,如狄更斯、如谷崎润一郎等等,好像有些书写的奥秘以及作品的线索收藏在这里,也确实多多少少真的如此——书写的实际环境高高低低、幸与不幸不一。但大体上我们仍可以归结出来:一、早年一个成功写出来(没成功之前就不确定了)的书写者,所过的日子的确好一些乃至于好不少,相对于彼时人们的一般生活水平,这不啰唆直接显示,普世地来说,书写者的现实社会地位和经济力是在往下调降中没错;二、老实说,作品的成就,完全看不出来和其生活高下好坏有什么联系。
书写者跟一般人一样,渴望也有权要求过更好的生活,以至于从他们自己的发言里,我们并不容易分离出来,哪些是书写的、哪些其实是一般生活的;还有,年龄也是另一个变动要素,如《礼记》时代就知道的,人在不同年纪对生命条件有不一样的需求及其承受力,寻常的四季流转气温变化,年轻时可不当回事还觉得好玩,到一定年岁就晓得那是生命持续存活的一次又一次考验,身体里某处、某个东西可能应声断掉。
安适的书写环境让书写稳定、专注、心不旁骛,可以的话应该这样,但有趣的是,书写一事就是没这么简单,尤其是文学书写——太过安适乃至于高出于当代人一大截的生活方式,对一个数学家、物理学家也许是纯粹的好事,但对一个文学书写者我们便不得不去留意其局限,这也正是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人的惊觉。普希金看到了写乌克兰民间生活的果戈理,托尔斯泰看到了贫穷还身背上一代债务的契诃夫,他们写出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完全写不来的东西,当然不是文学书写技艺,而是他们所在、所生活并了若指掌的那个更大世界。
这是文学书写的基本事实,文学史的ABC,书写者的社会位置往下调降,最终彻底离开宫廷取得(或被迫成为)独立身份散落于一般社会之中,书写的范畴却也因此亦步亦趋地不断扩大,及于一般人,及于边缘人,及于那一个又一个被忽视、被遗弃、被欺负被侮辱的人;书写者生活于哪里,那一个世界才打开来、进入到我们眼中。
从另一面看,冷血一点,这样的玩笑话因此也是对的——书写者过得太好,文学可能就不太好了;书写者有办法,文学书写就没办法了。

《尽头》,作者:唐诺,版本: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2
“我要写得更好,
这先于我想生活得更好”
我自己相信,真正的关键、接近于唯一的需求,正在于书写的专注、心不旁骛,这的确是个需要极高纯度专注、且长时间持续专注的困难幽微工作,以至于人很难同时真正追逐另外一个目标(当然,应付一般生活可以不是问题,书写者可别拿这个做张做致起来),像马克斯·韦伯劝诫我们的那样,你得认准这个生命中唯一的魔神,并专心侍奉祂一个。因此,书写者有限度的境遇好坏宁可只是命运问题,基本上取决于他活在哪个时代、哪种社会,乃至于个别地来说,被抛掷在哪一家庭,他所剩余为数已不多的心力智力(倒还不见得是时间),通常不足以改变此一命运的基本设定,也不用于改变它(真觉得好生活名流生活重要,就换个工作换个神吧)。所以,这不是背反决裂,而是人合理的、沉静的一种自我价值排序,是人可以做的选择:我要写得更好,这先于我想生活得更好。
我们说过这个,人可见未来的经济麻烦仍发生在生存线之上而非之下,在这样一个后文学后书写的年代,声誉无能且不断变质,书写领域的下滑速度也一定快过、大过平均值。我建议,以书写为志业的人可以自己稍微想一下整理一下,从心志到实际生活到和世界的关系设定,认真、严谨、朝向远方的书写仍是做得到的——真正到了完全不行的那一天,我们再一起来谈(或大声厉声疾呼)书写的公共意义和公共价值,谈书写对世界、对社会、对每个人的未来何等重要不可或缺,谈书写理当索取的报偿该得到社会多少物质支援财富支援等等。在这之前,我们仍然沉静、专心地、好好地写吧。
亚洲,尤其东亚这几个倾向于单一价值选择(比方相对于西欧)、较典型经济人式的社会,缺少蛛丝网般复杂多样价值信念的缠绕黏着拦阻,其相对下滑程度最为剧烈,这是我们当下的处境,台湾地区如此,日本也如此,这应该想成是全球较极端的特例呢?还是应该想成整个世界的领先指标?于此,中国大陆的现况是个例外,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的书写者极可能就是全世界物质待遇最好的,记忆里,台湾地区半世纪以来从未曾有过如此光景,日本有过,差不多到三岛由纪夫为止,那是书写者的华美年代,稍微像回事的作家都过着人上人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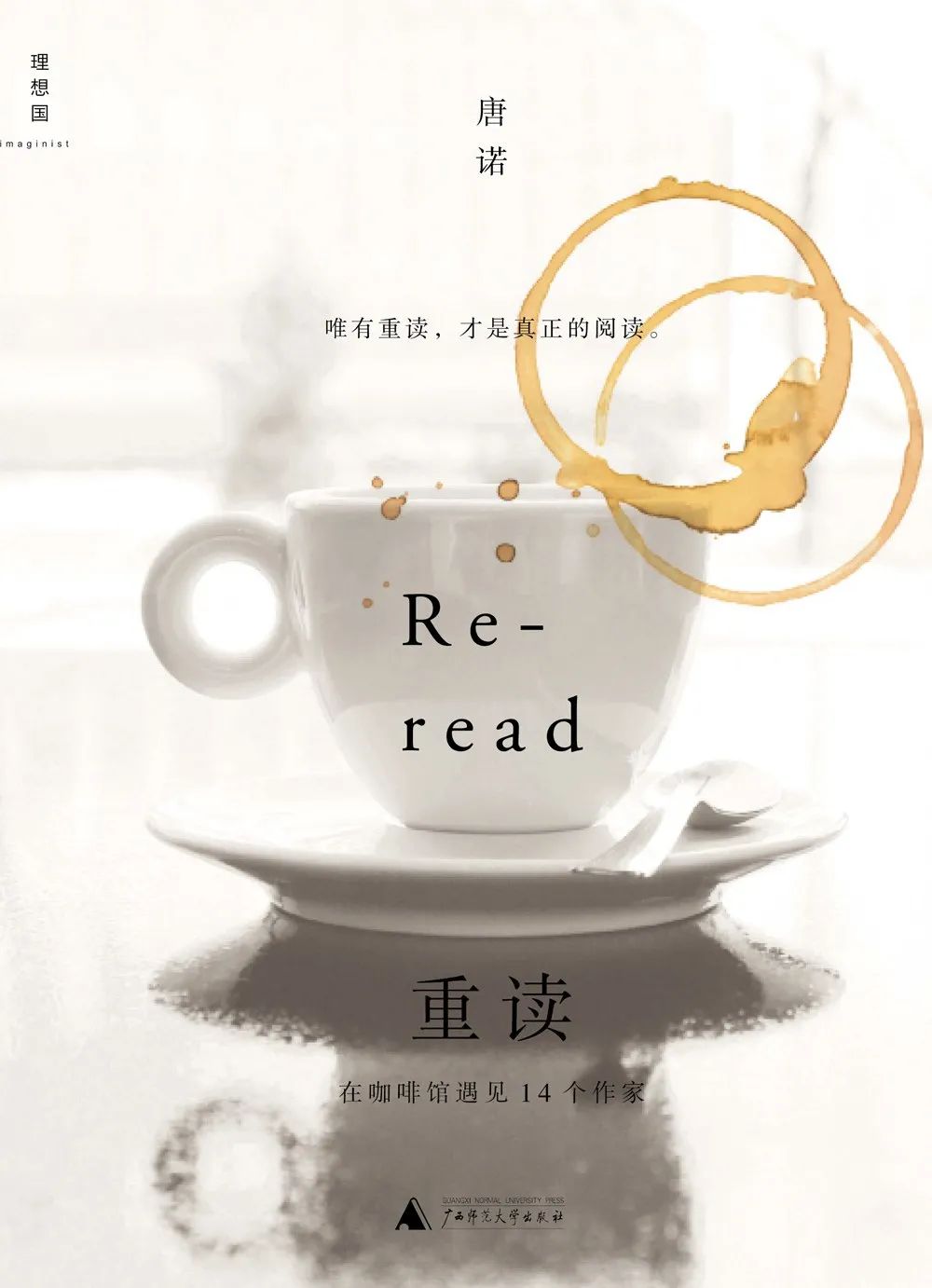
《重读》,作者:唐诺,版本: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
3
中国大陆书籍市场
正快速地往通俗倾斜
二○一三年冬天,我因《尽头》一书的出版去了趟北京,有一场和大陆的八○后年轻作家的谈话。我不认为中国大陆的如此书写好景会久留,我更相信这十三亿五的大书籍市场正走向M型化,快速地往通俗倾斜,这是结构性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我由此担心这批年轻书写者恰好处于一种较困难、较尴尬的转换时刻,他们容易残留着过度美好的记忆和期待如失乐园,让自己只不断感觉失意、沮丧、难以轻快地进入到一步步沉重起来的现实(得想办法让自己从身体到心智都轻快起来才行,如卡尔维诺以穿着飞鞋的珀尔修斯为例,这正是他的第一个叮咛)。我活过比他们长的时间,留意过一个个社会参差迂回但终归趋同的此一现实进展,以为有必要提醒他们一些事─我选了一个听起来不会舒服的题目,大致是“中国大陆当前书写的三个奢侈”:书写题材的奢侈,书写者声誉的奢侈(包括国内和国外),还有当然是书写物质报酬的奢侈。奢侈,意思是多于、高于“正常”,也就是不容易久留、可一直这样的东西,奢侈的最无可逃遁的危险正是成为一个习惯;这本来是好运,乃至于礼物,但一不小心就会转成陷阱、转为诅咒。
大概因此遭天谴了吧,当天下午谈话才结束,我就因胃出血送医,花了两整天考察了北京的医疗现状,并很不礼貌地取消了南下广州深圳的原行程,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广州深圳真长什么样子。
现在是二○一六年二月一日早晨,刚刚发生最有趣的事情是,台北市几天前下了雪,还有就是日本央行破天荒宣布“负利率”,比零更进一步,往后各银行得付日本央行货币保管费了,如同回到银行历史的最从前。当然,这仍是为着把货币赶出来,让日本钱淹脚目,再重重一次刺激消费。所谓“不完整复苏”的说法并不准确,还有点逃避事实真相的味道,真正的问题是,有效需求结构性的、长期性的不足。
来读博尔赫斯的这首诗,诗的名字就叫《诗两首》,其实是同一物的正反两面,没读错的话,说的应该就是诗人、书写者,乃至于博尔赫斯他自己,他带给这个世界的礼物和骚扰,他的欣喜和负咎,他的坚持和犹豫,他的昼和夜——
正面
你在睡着。这会儿醒了。
明灿的清晨带来初始的憧憬。
你早已忘却了维吉尔。那儿就是他的诗歌作品。
我为你带来了许多东西。
希腊人的四大根基:土、水、火、气。
一个女人的名字。
月亮的亲和。
地图的淡雅色泽。
具有陶冶净化功能的忘却。
挑挑拣拣并再次发现的记忆。
让我们觉得自己不会死去的习惯。
标记捉摸不到的时光的表盘和时针。
檀香的芬芳。
被我们不无虚荣称之为形而上学的疑虑。
你的手期望抓取的手杖柄。
葡萄和蜂蜜的滋味。
反面
想起一个睡着的人
是一件普通而常见
却又让人内心震颤的事情。
想起一个睡着的人
就是将自己没有晨昏的
光阴世界的无边囚禁
强加给别人,
就是向其表明
自己是囿于一个将其公之于世的名字、
囿于往昔累积的人或物,
就是骚扰他的永恒,
就是让他承受世纪和星辰的重负。
就是为岁月再造一个往事难忘的乞丐,
就是亵渎忘川的清流。
我这一趟关于声誉(以及财富和权势)的简单思索,先暂停在这里。
本文内容经出版社授权节选自《声誉》一书。原文作者:唐诺;摘编:张进;编辑:张不退;导语部分校对:赵琳。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唐诺首都体育馆 :书写者过得太好,文学可能就不太好了相关:
对于以创作为生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体力近日,日本著名设计师原研哉为小米设计的新Logo上了热搜,由于新Logo的设计仅仅是将原本正方形的边框“磨”成圆角,不少网友惊呼“雷总被骗钱了”。其实,原研哉的设计理念一贯如此,国人熟知的无印良品就是典型代表,简约、质朴,以物品本质的特征打动人心。原研哉本人也总是以“黑白”的极简形象示人,但他的性格并不沉闷,这从他1991到1995年在《小说新潮》中连载的设计散文中可以看出,本文便摘自于此。Running High(慢跑..
叶嘉莹:我一生遭遇的挫折,都是用李商隐的诗化解的我遭遇到很多人生中的挫折、苦难、不幸的事情,我都是用李商隐的诗来化解,但是你要看我是怎么样从李商隐的那种悲观的心态里慢慢地转化出来的。李商隐的诗大半都是悲哀、伤感的诗,以后我们会介绍李商隐的生平,看看李商隐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忧郁、悲观的性格。我当年也曾经喜欢过李商隐的忧郁、悲观的性格,可是我后来从李商隐的忧郁、悲观中转化出来了。我们慢慢地看。李商隐画像不是说“梦中得句”吗?有两首已经讲过了,还有第..
不能出国旅行的日子,书就是你的机票不久前,新周刊九行“旅行家”栏目采访了旅行作家尼佬,和他聊了聊大流行时期的旅行(点击左边超链即可重温)。那时,尼佬刚走完一趟滇藏小环线,话题就围绕着这趟旅行自然展开,结果采访主题在聊天中不断延展,原计划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进行到了两个半小时。尼佬非常健谈,不仅谈到了自己的旅行经历,还聊到了阅读,聊到了写作,当然也聊到了他对旅行文学的看法。在路上的时候,尼佬多用Kindle或手机阅读App读书。他最近在微博..
阅读小说能够提高共情能力吗?心理学家这样说在自媒体变成大众拿起来手机就会习惯性地刷上一刷的阅读盛宴后,我们读到了比从前多得多的或真实或虚构的故事。尽管阅读是为了获得知识,但是人们更容易对“给自己带来某种程度震惊”的故事(这也包括小说与艺术作品)投注更多个人情绪,然后基于这种情绪再发酵出大量的语言碎片。为什么我们会被别人讲述的故事打动呢,以至芮塔·菲尔斯基在《文学之用》中说,“震惊人的意识是一项费力的工作,绝非易事”。心理学家有他们的解释..
那些藏在唐诗宋词里的春色有哪些?以下文章来源于菊斋 ,作者任淡如本 文 约 4080 字阅 读 需 要 11 min周处《风土记》里说:“浙间风俗言春序正中,百花竞放,乃游赏之时,花朝月夕,世所常言。” 杨万里《诚斋诗话》里说:“东京(今河南开封)二月十二日花朝,为扑蝶会。” 《翰墨记》里说:“洛阳风俗,以二月二日为花朝节。士庶游玩,又为挑菜节。” 《光山县志》里说:二月二日,俗云‘小花朝’;十五日,云‘大花朝’”之说。但我们不须记得这..
简·奥斯汀:伊丽莎白是有史以来最讨人喜欢的书中角色1811年,东汉普郡五月的清晨,简·奥斯汀家的奥尔良李树正含苞待放。借着她的书信和亲人的回忆录,我想象出这样一幅画面:这位作家坐在她最喜爱的地方——靠近农庄大门的——一张胡桃木小多边桌旁,在一小沓稿纸上写作。一听到“吱呀”的开门声,她就迅速地收起了稿纸。这天,她的家人难得能给她一份清净,甚至安静。她娟秀的字迹涂满了一页又一页稿纸。她用笔蘸蘸墨水,执笔沉吟,草草写几笔又划掉、涂抹,然后再蘸蘸墨水。她写..
从兰波到瓦雷里,波德莱尔的继承者们自波德莱尔开启象征主义先河之后,法国相继出现几位杰出的象征派诗人,如“通灵者”兰波、“颓废”的魏尔伦、晦涩的马拉美,以及瓦雷里。他们继承波德莱尔的遗产,又通过个人探索创造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共同组成象征主义诗歌让人眩晕的多彩图案。新京报记者采访了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太胜,与他聊了聊波德莱尔的“继承者们”各自的特质、对象征主义诗歌的发展与继承。采写丨张进01“叛逆”表现于语言的激进让·尼..
波德莱尔:年轻诗人的致敬让我害怕得像一条狗当我们站在此时此地回看波德莱尔,回看《恶之花》,就像一场溯流而上的旅程,我们由此回到现代主义艺术的发端现场:一片新颖、茂盛且荆棘丛生的诗性森林,一个孤独、狂热又忧郁的灵魂。充满悖论的“恶之花”在巴黎长出,也只能在巴黎。大都市的繁华与荒芜、芳香与腐臭、光明与黑夜、希望与焦虑,共同容身在巴黎街头。波德莱尔迷恋地游荡其中,独自一人又被人群包裹。在这包裹中诗人警觉地睁大眼睛,在寻找着什么。“他寻找什么?..
叶嘉莹与顾随:师生情谊七十年葉嘉瑩在天津大劇院講座上講授古典詩詞师生情谊七十年叶嘉莹诸位老师、诸位同学:我非常高兴今天又来参加我们新年的晚会,同时还有我们两项奖学金的颁奖典礼。我今天想要讲一个师生情谊七十年的故事,因为今年是2012年。我出生在1924年,1941年十七岁考上了当时北平的辅仁大学。那时我们的系主任是余嘉锡先生,他教我们目录学,刘盼遂先生教我们经学史,陆颖明先生教我们声韵学,另外还有赵万里先生,他是王国维先生的学生,教我..
质疑观众,却又需要靠他们生存:罗兰·巴特眼中的先锋戏剧近日,一档戏剧类真人秀《戏剧新生活》让原本小众的戏剧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也让本就热爱戏剧的票友看到了戏剧更多的可能:离开华丽的布景、直面生存的压力、用最朴素的道具和最大胆的尝试打动人心。戏剧能带来新生活吗?60年前,罗兰·巴特就已给出过答案。原作者丨[法]罗兰•巴特摘编丨肖舒妍《罗兰·巴特论戏剧》, [法]罗兰•巴特著,译者: 罗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11月(点击书封可购买)01先锋戏剧之定义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