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也是王元化先生百年诞辰,学界素有“北钱南王”之称,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与吴琦幸《王元化传》适时出版,亦为一时雅事。
两书均为后辈追怀先师,王为钱先生私淑弟子,吴为王先生入室弟子,早前曾出版《王元化谈话录》《王元化晚年谈话录》等,已为传记撰写做了前期准备。去年推出40余万字《王元化传》,全景展现王元化的人生轨迹、人格特质、治学风格、处世心态,聚焦于作为文艺理论家与思想家的王先生求索、反思、否定、超越的艰难心路历程,特别是披露一些独家材料,又以史家的谨严考订过往的以讹传讹,相比此前出版过的《王元化画传》《王元化别传》等,该书呈现出后出转精,更为全面、客观、公正的特点。
读罢《王元化传》,掩书而叹,临风遥想。王先生学问既广且深,自非后学能登堂奥,探细微,现仅就王先生的精神底色略陈己见。所谓底色,特指个体从出生到青少年时期,由本我到自我、超我过渡的精神烙印。而贯穿王先生跌宕起伏的人生,决定其由左翼青年升华为深邃思想家的独特人生轨迹的,可以溯源到童年时期的三重底色:楚人血统、教会家庭、清园情结。
撰文丨陈建华(湖北经济学院)
01
楚人血统
传承屈原的孤往精神

《王元化传》
作者:吴琦幸
版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0年11月
王元化先生祖籍湖北江陵,出生在武昌,晚年王元化多次说到血管里继承了楚人传统:脾气暴烈、性格倔强。他常讲:“我是湖北人,性格中有楚蛮之气。王先生曾随汪公严习《离骚》,又以《文心雕龙》研究名闻学界。刘勰曾列出后世学屈骚的四类人:“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在鲁迅看来:“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王拈出鲁迅评价,引为同道,意在批判俗世仅将文学视为炫才耀技、吟风弄月之具,不能、不敢学屈子精神实质。严格地说,屈、宋固然分道扬镳,汉代贾谊却有屈子风神,后世追摹屈子者也代不乏人。王先生亦曾以屈原誉顾准“灵均将逝,脑海波起……茫洋在前,顾忌皆去”,他本人又何尝不是传承屈子精神的代表?也许是“日用而不知”,即前所言集体无意识,现略为申说——
王先生一辈子恶紫夺朱、恶郑声乱雅乐与屈原喜善鸟香草、恶怨禽臭物一脉相承。他一生爱雅如命、嫉俗如仇,他心仪十九世纪文学,自称十九世纪之子,尤其服膺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书中主人公热情豪放、倔强不屈,不向命运低头、不向恶劣环境妥协,分明就是屈子的异国知音。文学应指明向上一路,引人思考,展现崇高的精神力量,这是王一生秉持的理念。他对于张爱玲与钱锺书小说的批评正立足于此。晚年王先生更是对古老文明的衰落与人文精神的式微忧心忡忡。他并非反对大众文化本身,却担忧其艺术品位与精神向度:“艺术不能在古与今、中与外、新与旧之间作出高下之分,而只有崇高与渺小、优美与卑陋、隽永与平庸的区别”,“一个以时尚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是没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
楚人血统还赋予王先生孤往精神。孤往精神,是大儒熊十力揭示的治学门径。鲁迅有诗:“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萧艾遍地,标准混乱,众口嚣嚣,醒者彷徨无依。但真正的学术研究,须高视阔步,勇敢地走窄门,依自不依他,遵从内心指引,不以多数人的评判与裁断为意。王先生晚年主编《学术集林》,本可拉山头,搞派系,但他不屑于此;90年代他的“中道”和反思,也引来一些议论,被外人误解为“转向”、被划入国学派、保守主义等等。对此他感到气愤,郑重声明:“现在学术界也有拉帮结派之风,但我不参加互助组,也不参加合作社,准备单干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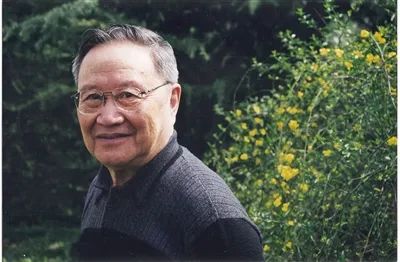
王元化(1920年11月30日-2008年5月9日),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
02
教会家庭
反思理性的局限性
王元化出生的家庭深受西方教会教育影响:父亲王芳荃少时家贫,得教会资助,为上海圣约翰大学首届毕业生,后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母亲桂月华曾在上海圣玛丽学校就读,外祖父则为一名传教士,曾为沙市圣公会第一任会长。王元化出生即受洗,成长于基督教及中国士大夫传统教育的家族氛围之中,虽然王元化从少年时代受到左翼思潮影响,参加革命之后,就抛弃了基督教信仰,但其人格、学术、思想难免受其影响。
吴琦幸曾问王先生从基督教家庭到入党是不是信仰的根本转变,王元化作了肯定的回答,随后又说:“但基督教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至少给了我们的好处是人应该谦虚,人不可以和神一样……”
青紫荣身肥家,为世俗所尚,以夸市井小儿,钱锺书与王元化都曾位列高官,两人虽无意为官而命运阴差阳错。钱冷眼观世,埋首书斋,不以俗务为念,刻意保持文化遗民身份,他不需世俗荣誉的加冕,故而只挂名不问事,届满身退,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王先生肝肠似火,以救国救民为念,但权力一旦出界,政统凌驾道统,也宁可弃高位,只以聚徒讲学为乐,这未尝不是基督教“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的反映。
私意以为,王先生的三次反思也与基督教家庭背景有关。王晚年著述,偏爱用“思”与“反思”二词。诚如林同奇所言,反思对于他而言,不仅是一种思考方式,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未必不是痛苦的,因为反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曾经自以为是的自己。王先生可能借鉴了古代为己之学的精神传统,他反思的心理基石更可能源自他一再引用的莎士比亚:“上帝创人,为何要他先有了缺点,才成为人”,因为人不完美,对外既不必有偶像崇拜,对内则要不断反思、修补与完善自身。他后来一直为当年违心地写过批判胡风的文章而不安,这与晚年托尔斯泰的忏悔极为相似,而他同时代的学人,有的人选择拒不反思,把问题推到外因上,或是三缄其口,仿佛什么不曾发生过。
外界通常以为,王的第三次反思主要集中在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论四大目标上。垂暮之年王先生明言第三次反思的核心并非四大目标,而是尚未完成的有关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人有局限,不是万能的,对于认识世界不能过于自信,须怀有一种敬畏之心和怀疑之心。他早年受到黑格尔思想影响甚巨,坚信人的理性可以达到全知全能。人们按照理性的指引,可以打碎旧世界,建立一个理想的新世界。而二十世纪的人类和中国的悲剧,在在说明理性同样造成了诸多罪恶。他于是忍受着刮骨疗毒般的痛苦,清理黑格尔思想中绝对主义和独断论。

王元化学馆内的王元化雕像。
03
清园情结
大学问背后有深邃关怀
幼时成长的清园,构成了王元化一生的第三重精神底色。吴著详细考订了王父王芳荃及清华诸贤的具体居住地的说法。晚年王先生对清园有一种特殊的眷恋,足以证明清园在王先生精神坐标中的重要地位。许纪霖说,“和王先生精神源头联系在一起的是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王并非清华弟子而是清华子弟,他认同清华,不是校友对母校的崇拜,而在耳濡目染的纯正学统,那是经由王国维所实践又由陈寅恪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氏为王国维纪念碑所写碑文,1990年代王先生常常反复吟诵,并在演讲中奋力鼓吹,文章中反复引用,可见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清华精神。他努力捍卫这种精神,他所担扰的,也恰是清华诸贤所开创的学统被有意或无意地毁弃。章太炎论清学衰败时指出,“其故实乃学者心术已不正,专门以刺探贵人意志为应对之资,风气败坏,学术自亦凋零”,可谓一语中的。民国最重要的文明成果之一,即在于,随着现代学术独立潮流与客观主义原则的建立,人文社会科学逐渐摆脱非学术因素干扰,成为独立自主的学问,向着专业化、学院化与独立化方面良性发展。陈寅恪晚年所坚持的,王元化通过对陈的阐扬所倡导并践行的,也在于此。
一些学者没能深入历史现场与王先生的心理世界,断言“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是正确的废话,显然低估了王的格局、眼界与胸襟。王晚年最忧虑的、谈得最多的问题之一是思想与学术的分离。八十年代各路人马放言义理,高谈阔论,“尊德性”压倒“道问学”,其弊在空疏,甚至游谈无根;九十年代形势丕变,“道问学”压倒“尊德性”,以考据代义理,以文献主义掩饰思想的贫乏,将学问变成工匠般的雕虫小技。睹此二十年的巨大摇摆,王先生将目光返归清园,他推崇陈氏,“陈寅恪我是真佩服,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冬烘先生,这个人很有历史眼光的”,一般人以为陈氏只是一个考据家,史料占有丰富,繁琐冗长,不成体系,王先生认为陈氏的独家本领在于,于错综的历史现象中,探索主要环节,掌握史事演变,于小事见大局。这种尺幅千里的功夫,实为其史学的最高境界,其大学问背后有穿破时代的深邃关怀,堪称“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之典范。
对于王先生丰富的一生,用三个向度概括,难免有简单化与标签化之嫌,挂一而漏万,不足以理解其广阔的交游与思想的脉落。好在吴著立体地展现了王由革命者、文艺理论家、到上海精神领袖的人生轨迹,读者自可涵泳与体味中寻找答案。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陈建华;编辑:李永博;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王元香坂景子 化的三重精神底色相关:
“听说你们城里有买那种隆胸霜的?”图片来源:公众号@喵呜不停《散步》有一天我妈从地里回来,反复向我夸赞今天遇到的一只神猫:“它寸步不离地跟着人走。人到哪儿,它也到哪儿。我都见过它好几次了,每次都是这样。”我说:“这有什么稀奇的。”她问:“那你见过整天跟着人到处跑的猫吗?”我细细一想,啧,还真没见过。我见过的猫统统特立独行,只有人跟着跑的份儿,哪能忍受给人类当走狗——哦不,走猫。我见过的猫,除非生命遭到威胁——比如天气极寒,或受伤..
历史上最后一个“侠客”时代《侠隐》:武侠文化为什么迷人文/韩松落很多人都有过武侠梦,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长大的我们,都曾读过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独孤红、陈青云,看过很多武侠片,对狄龙、姜大卫、施思、苗可秀像老友一样熟悉。很多人不只满足于读和看,而是已经身体力行地开始练武了。我曾在后院空地上照着《武林》杂志上的拳谱练武,还有好几个朋友曾经逃学到少林寺去学武术,在少年的心中,似乎技艺一旦修成,整个世界都会任我游走,再也..
辛德勇:有所立就必须先有破自 序《辛德勇读书随笔集》系列中的这一册《史事与史笔》,大致包括如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论述一些历史问题;二是讲说自己出版的一些书,所谓“史笔”,是指这些书的写法。这些文稿所述及的历史问题,看起来比较零落,相互之间没有多大联系。这当然是由于我没有定性,做研究没有计划和目标,因而也就没有确定的主题和范围,遇到什么好玩的问题就研究,高兴了就随手写下一篇,所以就成不了一个体系。我“起家”的学术专业是历史..
世界睡眠日专题:深夜不想睡,白天不想起2001年,国际精神卫生和神经科学基金会主办的全球睡眠和健康计划发起了一项关注人类睡眠的全球性活动,并将每年的3月21日定为“世界睡眠日”。2003年,世界睡眠日正式进入中国。每年的世界睡眠日,人们都会赋予它一个独特的主题。什么是当下人们睡眠的主题?恐怕是“失去睡眠”。根据2020年喜临门中国睡眠指数,我国国民平均睡眠时长仅为6.92小时,相比2013年减少了1.58小时。人们的入睡时间通常迟至凌晨,同时,拥有深度睡眠的..
我们的一种“不幸”,在于只能活在自己的时代里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一种“不幸”,那就是生命是有限的,我们只能活在自己的时代里。但可幸的是,我们可以借由历史去回顾、去检测人类经验的广度,去寻找生命的诸多可能性。可惜的是,往常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总是倾向去寻找标准答案,寻求某种盖棺定论的确定性,甚至会因为找不到确切答案而焦虑。然而,我们不曾留意的是,就算能够获得所谓的“确定”,或许也会因过度设限,反而失去了探知生命多样的可能。在看理..
春分:一曲清歌无误顾,浅黛春山处处纱倏尔春分已至。从云贵回京,也有两天了。沙尘暴之后,北京的花还只开了迎春、连翘、早樱和紫叶李,路边刚有一点明黄淡粉的春意,却连日阴沉,不见日头也迟迟不雨,仿佛时间都在这料峭的倒春寒里冻住,我却已踏遍了祖国西南的春色归来了。想起刚过去的带父母同游的半个月,恍惚间却像是做了一场梦。上一次写惊蛰还是和他们一同坐车从娄底去贵阳,在两个多小时的高铁上完成文稿最后的改定;再回北京,竟然已经是下一个节气了。分者..
“凝视这匹失明的老马,让我看见年迈母亲的样子”又是一年春季,再过几天就是春分了。而六年前的春天,一如以往,约翰·伯格(John Berger)是在阿尔卑斯小镇昆西度过的。他的忘年好友蒂尔达·斯文顿携团队造访,拍摄他在乡村的宁静生活。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会是他生前最后的影像记录,他的人生也只剩下两个春天了。这部影片叫做《昆西四季:约翰·伯格的四张肖像》(The Seasons in Quincy: Four Portraits of John Berger),春天只是其中一个章节。蒂尔达坐在木桌前..
农村大学生是该选择留在大城市还是回老家?“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其核心是要实现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资源的均等化,使农村的工作生活水平不亚于大城市。哪一天农村大学生及其父辈不再把在城市体面生活当作梦想,使他们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没脸回家”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吕德文《基层中国》1农村毕业生成为就业“夹心层”每年临近春节,在外漂泊的亿万年轻人都会踏上归乡的旅程。对他们中的很多人而言,“回家”既让人感到温暖令人向..
“殊死搏斗”或“虚张声势”:动物繁殖斗争图鉴当一只动物被天敌逼入绝境,它会奋起争斗。这可能是我们熟悉的场景。不过,同一种动物之间的个体斗争其实才最普遍,绝大多数都发生在春天这一繁殖季节。二十世纪生物学家尼可拉斯·廷伯根在行为科学奠基之作《动物的社会行为》将其称为“繁殖争斗”,并作了开创性的发现和探索。以下内容经华夏出版社授权节选自《动物的社会行为》一书。摘编有删节。尼可拉斯·廷伯根(Nikolaas Tinbergen,1907-1988),荷兰裔英国动物学家与鸟..
从B站学习直播到CoStudy,抱团自习何以流行?学习当然是我们每个人作为个体在学习,也就是在“自己学”,但是,学习却又经常是在群体中完成的。从离开家门进入教室那一刻起,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就在和其他人一起朗读、复习,即便放学回家,也可能会去同学家做作业。这是一种共同记忆。到了大学,到图书馆似乎才可能静下心复习,不然“缺少学习的氛围”。如果已经毕业工作,报名参加各类技能考试、考公,也可能会感叹“缺少学习的氛围”。大概为了营造这样的氛围,当直播兴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