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郑振满,厦大历史学系教授
民间历史文献是普通民众使用的文字资料,似乎与“文史哲”传统相去甚远,难以登大雅之堂。不过,我们从事民间历史文献的教学与研究,总是觉得其中有一套通用的话语系统,来自于源远流长的经史传统,或者说是中国本土的文史哲传统。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古代的经史传统,实际上也就不能真正读懂民间历史文献。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史哲传统 (经史传统)同样可以作为研究民间历史文献的方法。我在这里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民间历史文献如何使用经史传统,二是经史传统如何进入民间历史文献, 三是如何从经史传统研究民间历史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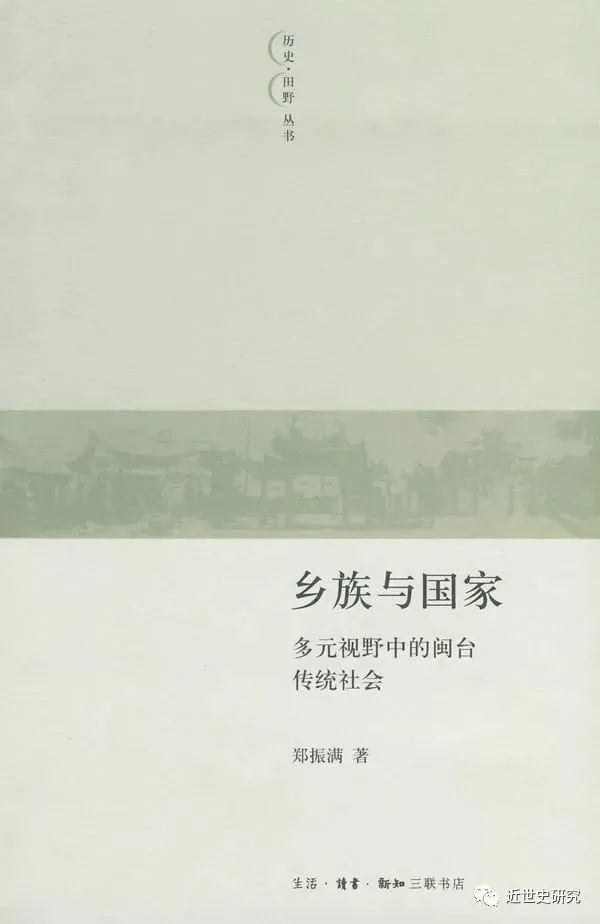
我们读民间历史文献,不管是碑刻、族谱、契约文书,还是唱本、剧本、宗教科仪书,大概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就是人、事、理。通常第一层是讲大道理,引经据典,拉大旗作虎皮,给自己一个立足点;第二层是讲事情,交代事情的经过、做法等等;第三层是讲人,交代相关的当事人,或者是相关的社会群体。每一类文献都会涉及这三个层次,这可能是我们世代相传的文本传统。我们读每一类文献,都要尽可能把这三个层次打通,搞清楚人、事、理之间的关系。
其实,在很多民间文献中,人、事、理之间是矛盾的,是脱节的,是说不通的,但那些编纂民间文献的高手,总是有办法自圆其说,把这几层关系说清楚。比如说拜一个神,可能根本就是荒诞不经、来历不明,他也可以引用祭法、引用道经、引用佛经,说出一通应该拜的道理。刘志伟经常说人家的祖先是假的,他们的谱系是伪造的,可是人家就是信以为真,当地人也都能够接受,这背后是什么道理?我们知道有很多民间文献是假的,但关键是为什么要造假?如何去造假?这里有一些基本的逻辑,我们需要搞清楚。有些道理古人是很清楚的,耳熟能详,随手拈来,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搞不明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说、这么做。因此,如果我们要读懂民间文献,就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回到中国本土的文史哲传统。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提出要做“乡族”的研究。“乡族”是中国本土的概念,很多民间文献都出现了这个概念。我的老师傅衣凌教授首先发现和使用这个概念进行研究,写了很多文章,提出“乡族”理论,用“乡族集团”“乡族势力”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我原来以为只要读了傅先生的文章,就可以研究“乡族”。可是傅先生告诉我,如果你要研究“乡族”,应该先去读“三礼”。“三礼”就是《周礼》《仪礼》《礼记》,都是先秦的儒家经典。我当时学的是明清社会经济史,可是傅先生要我去读“三礼”,实在是想不通,只好硬着头皮去读。后来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乡族”,其实源头就在“三礼”之中。
“三礼”记载礼仪秩序,这种礼仪秩序是为政治制度服务的,家、国、天下,无所不包,实际上是一套治国平天下的大理论。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中国传统的礼仪每年都有那么多仪式,祭天、祭地、祭山、祭水、祭祖先、祭鬼神,怎么忙得过来?后来才慢慢明白,不是所有人都要做这么多仪式,每个人要做的仪式是不一样的。在特定的政治体制中,谁应该拜什么,在哪里拜,怎么拜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这背后是一套社会秩序。通过礼仪系统维护社会秩序,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逻辑。当然,在不同的时代,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都会发生变化,礼仪系统也会不断变革和重组。
中国古代文人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引经据典,所以经典的影响特别深远。先秦时代的礼仪系统,在后世大多是行不通的,但很少受到质疑。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都可以重新解释经典,却不可以否定经典。所谓“六经注我” “我注六经”,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我曾经花了很多工夫试图搞清楚从“三礼”到“乡族”的历史脉络,后来发现,“三礼”的礼仪系统完全不适合“乡族” 的发展,“乡族”的礼仪系统是在“三礼”之外重建的。例如,依据“三礼”的规定,老百姓是不能拜祖先的,当然也就不能做宗族。到了宋代,程朱理学提倡礼仪改革,让老百姓都可以拜祖先、做宗族。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理论依据是《礼记·大传》:“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这原来是一套贵族社会的宗法理论,但程朱却把它移植到民间社会,我称之为“宗法伦理的庶民化”。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使经典可以与时俱进,不断获得新的意义。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我们的经典没人读了,我们的经史传统是否还存在呢?前几年,我们申请了一个教育部的重大课题,名称就是“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我们认为,在现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原有的传统已经断了,但在民间社会中仍有传承。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民间历史文献,找到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个课题已经完成了,但是成果还没出版,因为涉及的问题太多,还要补充、修改。我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各种民间文献的编造过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究竟是谁在编造民间文献?编造了哪些民间文献?为什么编造这些文献?它们承载了哪些传统文化?这就是我们试图回答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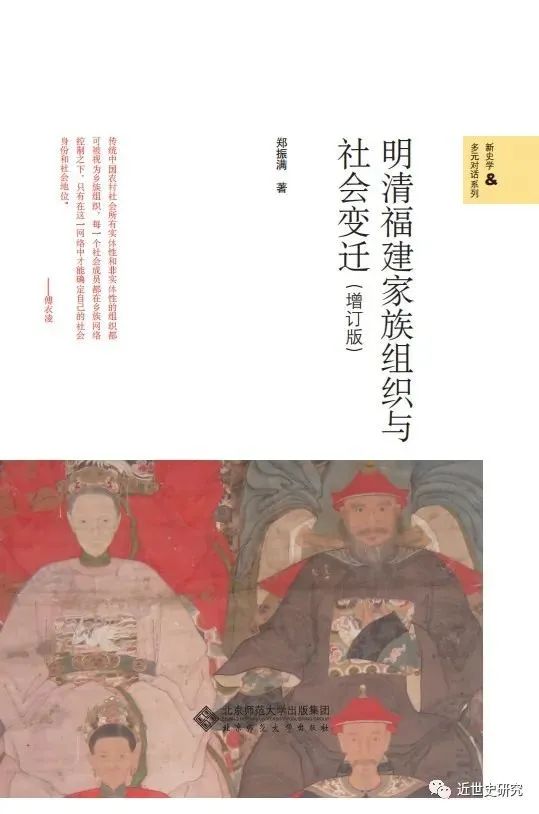
我们考察经史传统进入民间文献的过程,首先应该关注科举制度的教化功能。早期民间文献的作者大多受过科举教育,他们从小熟读经史,自然会把儒家经典运用到民间文献中去。他们的作品后来成为范本,不断地被传抄和模仿,逐渐形成一些流行的套路。我们研究民间文献,经常很头疼,觉得套话太多,似曾相识,有时就跳过去了。但是,这些套话实际上就是约定俗成的话语系统,对民间社会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把这些套话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我们就可以明白民间如何理解、使用经典,就可以了解经史传统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
明清时期有各种不同版本的日用类书,如《酬世锦囊》《家礼集成》之类,为民间文献的制作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活套”。由于这些“活套”的广泛流行,即使是识字不多的普通人,也可以阅读、使用、制作民间文献。根据最近的研究成果,大多数民间文献中的常用字并不多,大约只有几百字至一千字左右,读过私塾、社学的普通人大多能够掌握。《酬世锦囊》之类的日用类书,主要是为识字不多的普通人编纂的礼仪文本,这就为“礼仪下乡”提供了便捷的途径。此外还有一个历史背景,明清时期造纸业和印刷业的快速发展,降低了书籍的成本,扩大了普通人的阅读范围,推进了经史传统的普及过程。
我们以前有个误解,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识字率很低,文字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不大。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可以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有文字的世界,一个是没有文字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是互相隔离的,各有不同的运作机制。可是我们现在发现,中国各地都有大量的民间历史文献,可见普通民众早就进入了文字世界,而且他们很会利用文字,不断为自己制作各种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文字资料。我们在乡村做田野调查时经常发现,有的地方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历史文献资料,有时一家人就可以拿出几箱、几袋历史文献。这些历史文献大多是世代相传的,乡民的日常生活深受文字传统的影响。
还应该指出,在乡村社会中,即使只有少数读书人,文字传统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我小时候在乡下,经常听老人家讲故事、唱歌词,他们的知识系统主要来自于唱本、剧本、话本小说。乡下人吵架、骂人、教育小孩,经常引用历史典故和戏剧故事。以前有很多民间艺人、仪式专家、乡村文化人,他们可能读书不多,但很会利用文字资源,创作了大量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作品。这些民间文艺作品大多注重道德教化,同样是经史传统的重要载体。
最后,我想讨论如何从经史传统来研究民间历史文献。前面已经说过,民间文献通常要讲大道理,这些大道理主要来自于经史传统。换句话说,经史传统为民间文献提供了话语系统,或者说是民间文献的基本“语法”。我把民间历史文献的这种论述方式归纳为“对口型”。那么,究竟如何“对口型”?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大概有三种基本的套路。第一种套路是和现行制度相对应,尽可能找到合法性依据;第二种是和儒家经典相对应,尽可能找到合理性依据;第三种是和人情世故相对应,尽可能找到实用性依据。因此,我们只有把民间历史文献纳入特定的国家制度、儒家经典和历史情境之中,才有可能得到全面、准确的认识。
这里提出的民间历史文献的三种论述方式,类似于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情、理、法”。不过,从各种民间文献呈现的优先顺序看,似乎应该是“法、理、情”。例如,为地方神写碑记,最好是要找到其纳入祀典的依据,或者是发现其曾经受到国家的敕封;其次是依据《礼记·祭法》,在“法施于民”“以死勤事” “以劳定国” “能御大灾” “能捍大患”之类的条款中找到合适的理由;再次是依据民情习俗,列举其灵验事迹,指出其香火兴旺、广受信仰等等。实际上,大多数地方神从未纳入祀典、受过敕封,因此很容易被列为“淫祀”,遭到禁毁。那么,能否从儒家经典和人情世故出发,找到立庙奉祀的依据,就是考验碑记作者的时候了。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可以同时使用多种论述方式。比如编族谱、拜祖先,如果传承谱系很清楚,那就按宗法制度来讲,谁是高祖,谁是曾祖,谁是大房,谁是二房,等等;如果传承世系不清楚,那就找历史名人,挂靠郡望、堂号,或者是借用别人的谱系,联宗通谱;如果这些都行不通,那就借助地方习俗,编造收养、招赘、过继之类的故事,尽可能自圆其说。有时在同一部族谱中,可以同时看到这几种论述方式并行而不悖。这就是说,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这几种套路都是建构宗族的有效做法,都可以得到社会认可。
在台湾的台南地区有三种庙宇,第一种是“祀典”某某庙,第二种是“开台”某某庙,第三种是“玉封” 某某庙。这些庙宇一般都有碑记,介绍庙宇的来历和灵验故事。所谓祀典庙,原来是官方庙宇,曾经纳入祀典;所谓开台庙,据说是最早在台湾建立的民间庙宇,一般都是为特定地方神而建的;所谓玉封庙,据说是由玉皇大帝敕封的,一般是通过战童降神获得封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多种话语系统的并存,也可以看到民间社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我们力求从经史传统解读民间文献,主要是为了厘清民间文献的话语系统,探讨民间文献的论述方式。当然,民间文献在“对口型”的同时,已经表达了作者、编者们对经史传统的理解和解释,这对我们研究中国的文史哲传统是有意义的。尤其重要的是,民间历史文献中对于人、事、理关系的阐述,反映了普通民众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郑振满 | 民间历史文献与经史传optimal 统相关:
专访马德斌: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中理解经济在当下,“工业革命”已经是一个被扫进博物馆的古老议题。但其实,算下时间,它距今不过两百年,在人类史上只是弹指一挥间,而也就是在此期间,它被注意的程度在加速下降。而事实上,工业革命在经济史上是一个并未说尽的中心议题。它颠覆了生产的动力机制,塑造了经济的增长方式。不同经济体被拉开差距,形成一种“大分流”。追赶型经济体随后产生。经济学家马德斌把中国作为根本的方法,回到“大分流”前的中国和欧洲,比较工业..
在自足的北欧社会,宗教和世俗如何回应人生问题?北欧,作为我们社会文化的他者,不断凭借其完善的福利制度和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引发关注。一方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的预测,挪威、丹麦、冰岛、瑞典、芬兰的人均GDP均占据全球前十五,北欧各国优渥的生活水平及稳定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各国学习效法的目标。另一方面,北欧的人文内核也在多个层面引起热议,比如,在巨大的社会交往压力下,不少年轻人也自诩为“精神芬兰人”以表达自己的“社恐”属性。《芬兰人的噩梦:另..
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妙玉?妙玉,作为十二金钗正册在列的姑娘,无疑是最特别的那个。她既不是贾府的妯娌亲故,也不是贾府的座上客,她不是主人,也不是仆人,她是与红尘往来最格格不入而遗世独立的存在。妙玉的判词写道,“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妙玉因生来就有的病带发修行于佛门而从此远离世俗,可妙玉终究也不是僧人,所以她非僧非俗却又似僧似俗,“云空未必空”。而她的曲词竟叫“世难容”——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
隔离与超生:波拉尼奥和他的《智利之夜》波拉尼奥小说总出现名字冷僻的作家和画家,通过欧美死去和活着的诗人、学者和艺术家编织成典故横生、真伪杂糅的文本。如同小说主人公的自述,总表现出道德、精神、思想的自我隔离,波拉尼奥也想从传统中突围与超生。一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小说,专爱写文坛三事:文学评论、文学奖项和文学沙龙。前两者作为小说的取材,作家通常是不喜欢的,因其显而易见的无趣和专业化的归口,而文学沙龙是十八世纪欧洲文学的宠儿,普鲁斯特之后的..
安德烈·巴赞:改编电影不纯粹了吗?让我们回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电影发展之初看看安德烈·巴赞为“改编”这种“不纯粹”电影形式的辩护安德烈·巴赞回顾近10年到15年来的电影发展,不难发现一个日益显著的特征:取材于文学与戏剧。当然,电影从小说和戏剧中发掘素材早已有之,但那时电影的表现形式还是独树一帜的。《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和《三个火枪手》的改编,不同于《田园交响乐》、《宿命论者雅克》、《布劳涅森林的女人们》、《肉体的恶魔》、《乡村..
1919年的燕京大学,还不在颐和园路5号从明朝初年北京在现有城址上建成以来,北京“城”已经有了几张截然不同的面孔(图1),和这种形态差别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物理建设,最重要的,还是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活方式。在扩展出二环线以前,北京看上去还不是一块似乎会漫无边际扩展下去的大饼。多少年来,在外来者觊觎的眼光里,它都是黑乎乎的城门洞子里密致模糊的一团——大致说来,一直到民国初年,北京城市的发展还非常局限于那一圈城墙,为城墙铁桶般围定的那..
怎样才能将文学的触手伸向时代深处?女作家自有回答在这篇特别报道中,我们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茅盾文学奖评委张莉,以 8 位青年女性作家为引,结合她的阅读和持续推动女性写作发展的实践经验,探讨属于这个时代的女性写作,以及它的社会意义。但终究,我们还是要回到阅读中,才能找到答案。谈青年女性写作者的创作,不由想到她们的前辈:张洁、铁凝、王安忆、翟永明、林白、迟子建 …… 这些作家和她们的作品 ——《方舟》《玫瑰门》《永远有多远》《弟兄们》《..
近年影视剧里的民国服装,简直是漏洞百出说到民国服装,虽不过百年时间,而且尚有影像和图片资料,却多不为今人所熟悉。究其原因,是我们六十多年来几经政治风云和文化颠覆的缘故。仅以近年的各种影视剧而论,可以说是错谬百出。那些粗制滥造的姑且不论,就是精心打造的,也是漏洞百出。最为可笑的是不同时期的服装,出现在同一时代。仅以女学生的服装而言,那种上着月白或淡灰色的长袖短衫,下着黑色喇叭口百褶长裙、白袜布鞋的“五四装”竟然能出现在40年代末的示威游..
“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矿工诗人陈年喜陈年喜,陕西丹凤人,生于1970 年,高中学历。1990 年开始写诗。1999 年外出打工,成为十六巷道爆破工,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的矿山。2015 年因职业病另谋生路。2016 年获得第一届桂冠工人诗人奖。2016年陈年喜在纽约大学的演讲(节选):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写诗,稀稀拉拉也快三十年了。很多人好奇:你的生活几乎与诗万里之远,怎么会坚持这样一件无意义甚至是矫情的事情?我想说生命并不是逻辑的,尽管它有逻辑的成份在。再..
被沈昌文尊为老师的老师们2021年1月10日,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先生晨间梦中仙逝。消息传来,出版界、文化界、学界一片哀悼之声。创办《读书》、主持三联,许多文人学者因沈公受益。2015年出版的《师承集》一书收录了沈昌文与许多学人的往来书信,我们能从沈公与作者们真挚而务实的交流中了解《读书》的办刊理念,也能在感受到学人们的谦虚无私中,重返《读书》的黄金岁月。沈昌文,曾任知名文化杂志《读书》主编,著名出版家、文化学者。2021年1月10日离世,..